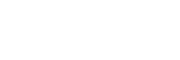《工人日报》关注贵州等省份易地扶贫搬迁:长在土地上的故事
- 作者:
- 编辑:肖慧
- 来源:当代先锋网
- 发布时间:2020-09-09 10:46:20
- 作者:
- 编辑:肖慧
- 来源:当代先锋网
- 发布时间:2020-09-09 10:46:20
9月9日,《工人日报》特稿关注了行走在贵州、甘肃等省份贫困山区的纪录片拍摄团队,讲述了纪录片视角下那些《长在土地上的故事》。通过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展现了易地扶贫搬迁大背景下人们的生活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巨变。

全文如下:
要联系上申周不容易——按之前约定的时间,连续好几天一遍遍拨打他的手机,始终无人应答。
等到他终于在千里之外按下接听键,通话开始的数分钟里,他都在重复一个意思:我不想接受任何采访。
2018年4月,反映贵州省极贫乡镇石朝乡脱贫攻坚进程的纪录片《出山记》上映。当年30岁的申周是片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按照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他和自己的父母从大山中搬到了县城里的集中安置点,成为当地又一例摘帽的贫困户。
2014年底,中国尚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农村。其后数年间,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每年都有1000多万人脱贫。这意味着,一些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几乎处于静止状态的农村,在最近不到十年时间里,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巨变。
在这期间,纪录片导演焦波和他的镜头始终没有离开农村。用他的话来说,自己的团队是“在土地上挖故事的人”。
如今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展示给任何人的申周,和许多少年、青年、老年一样,都曾是种在土地上的故事。

甘肃省西和县蒿林乡地处山区,是甘肃省40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到2019年,该乡12个行政村有9个实现整村脱贫。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王伟伟 摄
离与合
对于要不要搬迁,申家曾有严重的分歧。
“搬下去维持不了生活。”2016年初冬的一个晚上,申学王坐在灶台边,一边抽烟一边用最简洁又直接的理由否决了儿子申周的提议。
“搬下去的话,鸡、鸭、猪都不能养。”申母开口支持身旁的丈夫。
屋子的另一边,申周独自坚持着要搬到务川县城的想法。年满30岁还没找到一门亲事,他觉得这和深居大山家里条件太差有很大关系。“我还想成家,想有下一代,总不能代代都像这样过。”
三个人都沉默了,只有申母用火钳摆弄着灶炉里噼啪燃烧的柴火。
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是贵州省的极贫乡镇之一,申周一家所在的石朝乡大漆村多山地,少平原,再加上石漠化严重,人均耕地面积很少,是极贫乡里的极贫村。
大漆村里,村民大多只能靠牛羊等牲畜养殖勉强糊口。因为坐落在悬崖之上,直到2016年,村中的泉里组还没有通公路,村民出山需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离开大山,是申周心中改变命运的关键一步。而在焦波拍摄的多部聚焦农村的纪录片里,离开、留下还是返回,是不少农民需要做出选择的问题。
“那是俺爸爸的家吗?”头上绑着白布的小男孩问。
旁边的爷爷答道:“对了,这是你爸爸的家。”
“门口怎么这么小?”
“不小,这里头很宽敞。”
看着眼前的棺材,爷爷深深地叹了口气。
2012年,焦波的团队进驻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拍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村里一个叫张自军的年轻人到贵州打工,从8米高的架子上摔下来后不治身亡。骨灰下葬当天,做爷爷的就以这种方式向张自军年幼的孩子解释所发生的一切。
8年多过去了,焦波仍记得当时的场景,“强忍着情绪才拍了下去。”
“咱们山里的孩子出去打工,真是一件要命的事。”丧事结束后,杓峪村的“学问人”杜深忠十分感慨。年轻时,他也外出打工,五年时间掉了13颗牙齿,“就是拿着人肉换猪肉吃。”
今年初,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29077万人。这个群体的存在,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进步,一方面也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不过在杜深忠看来,农民工中有80%都是被“逼”着出去的。在焦波导演的数部纪录片中,“总比打工强”也是不少农民评判生活状态时说的一句话。
出门在外艰辛,返乡创业也不见得容易。16岁就外出打工的任庆金,为了照顾母亲和单亲女儿,回到老家——位于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大集镇的丁楼村。丁楼村位于鲁西南,过去是靠土地艰难讨生活的贫困山庄。近年来借着农村电商的风口,那里成了全国最大的儿童演出服饰生产基地。
2016年底,该村300户农户中,有280多户开有淘宝网店,年销售额超过100万元的有40多家,超过500万元的10家。
可任庆金没能赶上好时候。他起步晚,又不太会经营,网店开了没多久就因差评和投诉被封。原本用来做生意的电脑成了他玩游戏、喊麦的工具,女儿的幼儿园学费拖了两个月还没交上。
借钱无果,又数次与母亲争吵后,任庆金一气之下砸了键盘,注销了淘宝店。
挣的钱不够生活,“返乡”只是一件看上去很美的事情。

《出山记》一开始,申周(右一)一家在深山中的家门口吃饭。受访者供图
爱与恨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焦波团队正在云南山区拍摄新的纪录片。受此影响,直到7月下旬,他才返回北京。
“疫情来了,村子封了,摄制组正好在村里待着,一直拍到6月末。”焦波的农村纪录片,拍摄周期大多都以年计算。
今年已70岁的焦波出生在山东农村,作为农民的儿子,过去他总觉得自己很了解农村,也了解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但随着一部部纪录片的拍摄,他变得不那么肯定了。
杓峪村的主要经济作物是苹果。纪录片拍摄那一年,苹果滞销,杜深忠和老伴儿张兆珍用每斤2元3毛5分的价格“贱卖”掉苹果后,在家请来帮忙的同村人吃饭,那是杜深忠在整部纪录片中唯一一次喝酒。
“这些年我在果树上付出的努力已经很多很多,但花十分代价得不到三分收入。”借着酒劲,杜深忠激动地说。
不久后的年关,张兆珍在收拾家时翻出了杜深忠年轻时参加鲁迅文学院学习班的习作。“农民就是种地,咱搞文学这些东西是相当艰难的。”翻着泛黄的格子纸,杜深忠说了一番让人意外的话,“都说农民对土地有感情,我对土地一点感情也没有!就是没办法,无奈。”
“这个土地不养人,”杜深忠接着对正上大学的儿子杜海龙说,“这里的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
在几年后拍摄的《淘宝村——丁楼村的故事》中,有一幕是开网店受挫的任庆金骑着载货摩托车到田里收玉米。
“村里开网店的一多半都不种玉米了吧?”一边掰着玉米,他一边问同村的长者。
“电脑一响,订单就来,都忙着挣钱去了。”长者说。
“我要是一天能接500单,我也不干这个。”任庆金没好气地说。
焦波意识到,现实中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已让农民与土地间的天然连接变得复杂起来。
“春天他们播下种子,无论是丰收、减收甚至绝收,等到来年他们依旧在同一片耕地上继续播下种子。”焦波说,这其中藏着农民的挫败、无奈和坚持,不是简单“很苦”两个字就可以表达的。
不过依然有人眷恋着自己世代生活的土地。申周的父母为了修房子,把五大车石头、砖块一块块抱上墙。悬崖之上的大漆村泉里组,村民申学科的父亲身患重病,每次去务川县城看病都要几个人轮流背到山下坐车。即便如此,他依然和组里其他不少人一样,激烈反对搬迁。“我又不是别处搬家来这里的,我祖宗就在这个地方。移民搬迁也轮不到我们。”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这样说。
为了继续与土地、牛羊在一起,泉里组反反复复向村里和乡里要求修通进山的公路。
就连杜深忠,焦波也觉得他对土地是“爱之深,恨之切”。
看到村里人把古树卖到城里搞绿化,他愤愤地说“这叫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只看见钱了。”去地里收玉米,老伴儿抱怨玉米被獾糟蹋了,他却说獾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可恨的是那些卖假种子的人,今年这块地差一点就绝收了。”
骂声,泄露了这个老农微妙的情感。

目前,甘肃西和县通过发展辣椒育苗、栽植和蔬菜种植产业解决贫困问题。9月4日,一名农民正在日光棚里晾晒辣椒。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王伟伟 摄
变与不变
“我下去维持不了生活。”
“别人下去都能找活干,你们下去不能找活干?”
“下去我活不长久了,最多再活两三年。”
“下去怎么可能活不长久?你不要动不动就说活不长久。”
“你这是把我逼上梁山了。”
又一次因为搬不搬迁的问题产生争吵后,申家父子矛盾激化,差一点大打出手。大漆村党总支书记申修军闻讯前去调解,“因为移民搬迁,要是闹出事故来了,谁能负责?”
2015年,焦波收到一位年轻影迷转发的微信文章,大致内容是中国将有7000万贫困人口走出“大山”。焦波看后心里一惊,决定要拍下正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开展的脱贫攻坚工作。
《出山记》由此而来。
位于大山深处,在大漆村常常能见到云雾缭绕的景象。“我现在的处境就像眼前的迷雾一样看不清。”在拍摄前期走访时,只上过小学五年级的申周脱口而出的这句话,让焦波眼前一亮。
如此“格格不入”的场景,在《乡村里的中国》里也出现过。
纪录片拍摄那年,几乎没有声乐基础的杜深忠花近700元买了一把琵琶,却跟老伴儿说只花了不到500元。在杜深忠眼里,琵琶一看就有灵性,是他多年来想拥有的乐器。
秘密还是被张兆珍发现了。“就不该让你手里有钱。你为这个家庭想吗?家里谁没有褂子,谁没有袜子,谁没有裤子你知道吗?”
面对一连串的质问,杜深忠有些恼羞成怒,“这是高雅的东西,跟你说就是对牛弹琴!”
画面在琵琶发出的尖锐的响声中戛然而止。那种不和谐,很像杜深忠在杓峪村的处境——收入、经济水平越发成为衡量人之成败的重要标准,他的学问与爱好就越发显得尴尬。
身处飞速的变化之中,曾经最讲究在土地上规律、重复劳作的农民,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今年‘六一’我压了一批货,这次一定要赌一把,以前的发展方式太慢了。”任安存坐在电脑旁,盘算着当年夏天儿童演出服能不能卖到他计划中的七八百万元。
“如果现在不创业,再过几年,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任安存爱笑,笑起来的神情还有些人们印象中农民的腼腆。只是一开口说话,他就立马变成了年轻企业家的模样,还是特别有创业激情的那种。
“这里的网速竟然比上海还快!”上海一所高校的教师到丁楼村做调研时忍不住惊呼。
有意思的是,再大胆的想法和再快的网速,依然不能撼动一些深植于农村的朴素观念。
任恒家的服装加工厂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18岁那年父亲意外去世,他就退学回家与母亲一起经营淘宝店。性格和经历让任恒比同龄人成熟很多,他很快成为家里的顶梁柱,网店生意也做得小有规模。
不过在任恒母亲心里,还有更重要的规划。
“给你订不上婚,你爹又没了,我领着光棍儿子还有脸上街吗?”夏收后的一天夜里,母子俩一边在库房整理货物,一边又说到了订婚成家的事。
面对母亲安排的一次次相亲,尚未满20岁的任恒显得积极性不高。“这两年先把生意做好,再说订婚不行吗?”
“不行。给你订了婚,娶了媳妇,我说话才能硬气。”
城市中常见的催婚与反抗催婚的拉锯战没有上演。当年春节,任恒就与一个叫平平的姑娘订了婚,很快举行了婚礼。
新媳妇的到来填补了网店客服的空缺,也给家里带来了不少欢笑。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任恒依然遵循了农村地区早婚甚至早育的规律。
就像电子商务虽然看似改变了一切,却没能抹去丁楼村土地上原有的肌理一样。
又一个“六一”销售高峰过去后,重新振作起来经营网店的任庆金、最终没能实现计划销售额的任安存、新婚不久的任恒和丁楼村其他人一起,加入到抢收麦子的队伍中。
赤膊、挥汗,在土地面前,没有老板,只有劳动的人。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柏果树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儿童在打乒乓球。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雷宇翔 摄
战线上的人
经过申修军反复做工作,申学王和妻子终于转变了态度。2017年秋天,申家三口搬进了务川县城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今天是我们最好的日子,要感谢你。”申学王对前来帮忙搬家的申修军说。
在焦波的每一部农村纪录片里,村干部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出山记》中,申修军只有3个在家的场景,除此以外,他每一次出现在镜头中,都是因为有问题需要他解决。
石朝乡修大通道,沿途要拆除大漆村13栋居住房,申修军要到每一户家中做工作。悬崖上的泉里组是搬还是留,留下来的话怎么通公路,为此申修军跑了一趟又一趟。精准识别后,没成为贫困户的人有的去堵路,有的扯烂申修军的衣服,打得他全身多处“挂彩”。
即使回到家,申修军也还要面对妻子对他“不顾家”的数落与埋怨。平日对待最激动的村民都游刃有余的申修军,这时却讲不出让家人信服的道理。
为了给村里引入资金发展乡村旅游,杓峪村党支部书记张自恩四处奔忙,但个别村民老是以“查账”为名找他的麻烦。面对无休无止的审核,他气急败坏地说:“大不了写辞职,辞职不干了。”
在日渐富裕的丁楼村,村支书任庆生日子同样不好过。大集镇希望把村里的网店统一搬到镇里的电商产业园,村民想在自家责任田上建厂房。任庆生多方协调,却落得里外不是人,上级认为他开展工作不力,邻里间则说他是丁楼村的“叛徒”。
有观众质疑,这些画面是否在刻意美化基层干部,焦波却认为,基层干部当然有不同的横切面,但作为中国乡村治理最直接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绝不可忽视。“尤其是在脱贫攻坚期间,他们是真正将双脚踏在战线上的群体。”
在跟拍申修军期间,有一次摄制组夜里走进他办公室,正好拍到他一边打点滴一边填写当天要上报各级部门的各种材料,“白天处理各种事,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填表,经常要填到凌晨。”
这段画面没有被放在成片中,因为团队担心把申修军拍得太苦,“观众会觉得很假”。
张自恩最终没有“写辞职”,上级部门介入后,不实举报的事得到妥善解决。直到现在,他依然是杓峪村的党支部书记。
一直以来,杓峪村既不是贫困庄户也不是富裕农村,它就像传统中国农村典型的代表,既沐浴着时代的风雨,又似乎总是在原地静止着。
《乡村里的中国》拍摄8年后,除了多了零星几家民宿和农家乐,被张自恩寄予厚望的旅游产业并没有让杓峪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种苹果,依然像过去多年一样,是村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
“不过现在,我们已经能直播卖果子了。”张自恩说,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庄镇镇长为村里的苹果代言,一场直播卖出了不少库存。
为了下一代
《出山记》以申周一家在老屋吃饭开头,以搬迁后在新房吃饭收尾。“出山”后这家人的生活,成了留给观众的一个谜。
谜底并不算美好。因为不习惯也负担不起城里样样要花钱的生活,申学王和妻子一度隔一阵就回到山里,在曾经老屋所在的位置搭个临时帐篷养鸡养鸭。后来,当地政府给申母安排了一个保洁员的工作,再加上申学王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夫妻俩才慢慢不再往回跑。
但申母依然在安置房附近找了一块地,除了冬天,家里的菜都从地里出。她说,这样既可以补贴家用,也能打发时间。
把搬迁视作救命稻草的申周没能如愿。他不满足于政府安排的流水线工作,可限于学历又很难找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几经辗转,如今他还在务川周边的工地上做着零工。“住房条件改善了,可怎么成为城里人,我还没想到办法。”
至于他的亲事,依然没有眉目。
移民搬迁可以很快,但搬迁之后的磨合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
在云南,焦波团队记录了中国最后一个传统村落老窝村搬迁前后的场景。由于地处边陲,交通极为闭塞,老窝村140口人所过的生活几乎是任何一个现代人都难以想象出的贫困与落后。
面对镜头,15岁的初中辍学生邓志花说:“老天爷怎么让我出生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没让我在外面出生。”
“为了下一代”,几乎是每个易地扶贫移民搬迁户最深层的动力。
《乡村里的中国》上映后,杜深忠“红”了好一阵。不过60岁的年纪和肚子里算不上太多的墨水,让他的生活最终没有太大变化。8年过去,或许最让他欣慰的,是儿子杜海龙如他所愿,通过读书走出了农村。大学毕业后,杜海龙在北京找到工作,并正计划着在那里成家。
“杜深忠的下一代改变了命运,也许申周的下一代也能擦去眼前的迷雾。”焦波说,在老窝村的拍摄结束前,全村人从有滑坡泥石流风险的老村子搬到了新村。虽然只间隔两公里,但老窝新村一切都是新的,新的房屋,新的联通外界的公路,还有新的小学教室。
回到北京后,焦波团队粗剪出了《老窝》的样片。样片结尾,孩子们扯着嗓子朗诵《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镜头扫过那七八个孩子的脸。谁也不知道,等他们长大了,是否还有老窝村这个地名。
来源 工人日报
见习编辑 吴一凡
编辑 徐微微
编审 田旻佳 肖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