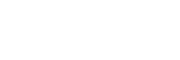亲情友情,“亲密有间”情方久
- 作者:罗兴武
- 编辑:徐微微
- 来源:当代先锋网
- 发布时间:2020-05-01 11:28:26
- 作者:罗兴武
- 编辑:徐微微
- 来源:当代先锋网
- 发布时间:2020-05-01 11:28: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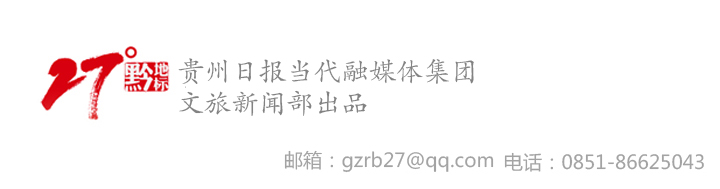
庆祥是我妹妹的儿子。上世纪70年代,我在武汉大学念书,他随堂祖父出差,半道上,堂祖父将他丟到我身边,一行人却潇洒着去了河南。
庆祥那时还不满5岁,而我的学业正待结束,作为毕业班学员,没心思也没时间照护他。在逼窄的学生宿舍里,我对他约法三章:不能哭闹,不能干扰,不能跑岀本宿舍大楼范围。这样,他大多时间只能老老实实“陪读”。
但小孩哪有不哭闹的呢?每当庆祥撒泼时,我就将他抱去操场中。那操场是个半拉子工程,尚末启用,长满荒草,我从窗口能看见场里的情形。我对他说:“耐心哭,哭累了自己回来。”起初,他会在那里干嚎一阵,估摸确实没人来打救了,便逐渐降了调门,后来大概在草丛中发现了蚂蚁或蟋蟀类,很快就投入到自己的乐趣中。我有时会忘了他的存在,待楼道响起敲击饭缸的声音时,才又猛然记起身边还有这样一件重要的事。
困难的问题还有每天的生活。武大学生食堂那时的中晚餐多是骨头炖藕块,几乎千篇一律,味道跟样式一样单调。为刺激胃口,同宿舍同学买来干辣椒,洗净,剪成小节,使劲加些盐,用凉开水泡在罐头玻璃瓶里,吃饭时在菜汤里掺点这样的辣椒水。庆祥也别无选择,将贵州人不怕辣的本事发挥得淋漓尽致。唯早上可不吃食堂打的稀饭馒头,去校门口买个油饼替代,这成为他一天的奢侈。
妹妹后来提及,庆祥从武汉回家后,有四个明显变化:一是与书交了朋友,二是早上不再睡懒觉,三是不再挑食,四是学会自己穿衣和简单收拾被褥。这些都像是歪打正着,那一个多月,当学生又当爹妈的日子,连滚带爬拉扯着走过,对他的所谓教育决非刻意而为。
说来有趣,庆祥后来便与武汉结缘。中学毕业,考进武汉一所大学,毕业后在贵州干了一阵,辞职去海南,但很快又去了武汉。之后,多种原因让他回贵阳,工作一阵后又去武汉读研究生。人生紧要处,潜意识里浮现出来的总是武汉。他在那里获得人生最初的一些朦胧印象,大武汉特别是万里长江奔腾不息的大气象,在头脑里怎么也抹不掉了。
他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省一个地质队,工作地点沉到遥远山区。当时我在省直某单位工作,给人错觉可能会有些能量。庆祥有调整一下工作单位至少是工作环境的愿望,我给他交底,要他立足于自强。后来,他辞职南下海南,到我们再见面时,他已有了女朋友小王。我问他工作近况,他说总在跳槽找更合适的事情。我说年轻时不跳几次槽,人生就太乏味了。他本以为要挨我尅几句的,没想到受到鼓励,一笑释前嫌,两老少什么都没再解释。
后来小王谋职,我依然爱莫能助,他们便打消了对我的企望。经过几年打拼,两口子在贵阳渐渐站稳了脚跟,庆祥进入一家上市公司,爱人从事会计职业,两人兢兢业业,悉心照料女儿,直到把女儿送进一所门槛颇高的高校留学深造。庆祥坦言,他曾经对我有过怨恨,正是这怨恨让他产生自立自强的冲动,有了后来的人生。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居然将我视为影响了他一生的人之一,对我在亲情方面的“冷漠”与固执,称赞说是思想观念更新,不仅坦然接受,而且认真实践,还倡导推而广之。
我同庆祥是亲情,却像朋友那样相处,形成了舅甥加朋友的特殊关系。亲情里有义务与责任,相互依赖的成分较重,双方容易陷入无奈与纠结,特别是对年轻人的锻炼成长没有好处。悟到这一点,我便有意让亲情淡化一点,以友情的方式来处理一些实际问题,尽可能获得超然与洒脱。因此,在我和庆祥之间,不失亲情,却也保持了适当距离。他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时,绝不会不管三七二十一,说:“谁叫你是我老舅呢?”我有什么事需要吆喝他时,也绝不会居高临下,颐指气使。
我前妻去世时,两个女儿尚小,庆祥第一个跑到我身边来照应,完全像自家儿子的样子。我退休后,有年生日临近,他说他给我做一次生日,我说不想过生呢,他说那我就请你吃顿饭,我说行,然后两边家人就聚了一次。我发了几篇小说散文,他是敢认真提出批评意见甚至调侃几句的人。我能体会到他对我的敬重,却从不阿谀。
我觉得这样挺好。
那次在武汉,我带庆祥去了一趟武汉长江大桥,同他在桥上照了张相。我抱他坐在桥栏上沿,用右手护着他。他和他父母亲都将此行视为他一生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仿佛那次相处是给我们一生定下了一个基调,无论后来的情况怎样,都已经无法改变相互关系的轨迹。我却在想,他在学校呆了一个多月,除了委屈,还真有什么收获吗?
文/罗兴武
文字编辑/陆青剑
视觉编辑/向秋樾
编审/李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