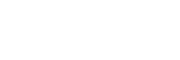【脱贫攻坚走基层】鱼跳:逆流而上的村庄
- 作者:肖郎平 谢巍娥 周自立
- 编辑:田旻佳
- 来源:当代先锋网
- 发布时间:2020-04-28 21:04:07
- 作者:肖郎平 谢巍娥 周自立
- 编辑:田旻佳
- 来源:当代先锋网
- 发布时间:2020-04-28 21:04:07
4月22日十点半,天上掉着不大不小的雨,雨点非常细密。60岁的张仕香,瘦弱的身躯包裹在深紫红色的皮夹克内,沿着公路边缘冒雨奔跑。他向路过的汽车招手,车没停。
隔三差五,他就从移民安置点的新家奔向8公里外的老家——鱼跳村。运气好的时候,能搭上便车少走一段路。
目的,仅仅为了回家放牛。有牛,才能耕地。为什么还要放牛耕地?他说,谁也不愿意这样辛苦,可是安置点没有就业机会,不得不两头跑继续种地。
恰如其名字寓意一样,鱼跳村的村民开启逆流而上的生活,有心酸往事的回忆,有当下尚未完全克服的艰辛,也有更多在适应中探索未来的希望。
鱼跳,最后的三公里
田坎彝族乡毕节市最东北的角落,也是七星关区辖区最远的乡,距离长达130多公里。这里地处川黔两省三县区(古蔺、金沙、七星关)的结合部。
从地图上来看,田坎是毕节的最东北角,而鱼跳又是田坎的最东北角。高耸险峻的大山和幽深峡谷中的赤水河,将几个不同省份的县区切割开来。我们决定去那里看看脱贫攻坚的情况如何。
导航软件显示,如果一早从市区出发,行程三个半小时,那么采访时间就受到很大限制。我们选择,4月21日晚夜宿临近的普宜镇,次日一早出发。
到了田坎彝族乡的大元村医务室,车到了路的尽头。我们才知道,鱼跳村已整体搬迁。16户53人中,有的搬到毕节市区,大部分搬到乡政府所在地,只有一个五保户老人还住在那里。
73岁的村民王正江说,大元村地理环境恶劣,背后的金银山是一座大石山大森林,大山夹着河沟,很难发展。种包谷还是刀耕火种,一亩只能收三四百斤。他通过电视了解到赫章海雀村的发展历程,“海雀都发展了,我们这种地方发展不起来。”
大石山留不住水,也留不住人。大山组400多村民,只有20多个老人在家,其他人都出去了。王正江说,“可能过二三十年就没人住了,那时候老人都不在了,年轻人都不愿意回来。”
老人觉得欣慰的是,村民衣食住行都解决了。过去用水要靠水窖蓄积天然降水,到1.3公里外的地方背饮用水。2010年开始,政府提水工程解决了这个大麻烦。“最大的变化是房子,过去都是夯土墙草房。共产党还是好,就算发展不起来,也饿不了饭。”
公路尽头是一段通往坟塆组还没硬化的毛路。大元村村民和村干部都坦言,群众对脱贫攻坚很满意,唯一不满意的就是这最后的三公里路三年仍未修好。乡党委书记吴付祥说,这段路已立项,得到福利彩票扶贫基金238万元的支持,今年6月30日之前一定能够完工。
从医务室到鱼跳村,比毛路还更为艰难,只有一尺宽的羊肠小道。而距离呢,大约也是三公里。很难用山路这个词来称呼它,因为山路无论如何盘旋总是有相对平缓的路段,而这条路其实是一直往下俯冲,从海拔1120米直降至海拔400多米。
鱼跳,让人望而生畏。气候反差之大是最好的注脚,山下冬暖夏热,山上冬冷夏凉。王正江说,他已经十多年没去过这个村子。
天依然下着雨,我们开始下坡时,张仕香急急匆匆飞奔而来。路太难太窄,泥泞易滑,不允许我和他一起打伞并肩缓行。他劝我们回去,路难走,天气又不好,“太遭罪了。”
鱼跳村的名字,缘于一个传说,鱼到了这里要往上跳才能过河。那一天,我们努力追随着张仕香,或走或跳或跑,奔向鱼跳村。

通往鱼跳村的路极其崎岖狭窄,最窄处,一道栅栏就能防止牛跑出山谷。
割舍不了的土地
两侧是灌木丛生无法穿越的高坡,夹缝中的路是唯一通道。一路上有两个木头栅栏,一个栅栏设在密林和山沟之间,一个栅栏竖立在很高的石坎前,农民用它们来防止牛跑出去。
一道简单的栅栏,就能让牛无路可逃,狭窄的程度可想而知。在这种地方生活一辈子是真的遭罪。路如此艰难,张仕香为什么还要冒雨跑回老家呢?
他说,回去养牛。牛平时不用管,直接放养在山上,天黑了自己会回牛棚里,隔三五天去看看。听起来,虽然辛苦点,但还是个不错的增收门路,就算一年卖两三头也有一两万元的净利。
仔细一问,其实不然。
准确地说,张仕香是放牛而不是养牛。他说,还要耕地,不养牛不行,“养牛卖?没有本钱!”
一路上,他在气喘吁吁地奔走中讲述生活的艰难。儿子五年前因打架而坐牢,儿媳改嫁,留下两个孙子。如今,大的孙子7岁,小的孙子5岁,儿子坐牢时小孙子还在娘肚子里。
搬出去没有就业岗位,一家人吃低保,但这点钱还不够。所以,他还是坚持两头跑,能种多少是多少。
站在村口眺望,房子已经基本拆除,偶有残垣断壁,复耕的屋基上种了蔬菜、玉米、小麦等。村子中央一座白墙黑瓦的房子最显眼,后面是五保户残破不堪的屋子。

房屋拆除后的屋基上种了玉米等作物,图中的三座山,从左至右分属于四川古蔺、贵州金沙和贵州七星关区。
进入村子,路边的第一个建筑物是坟。它太特别,别的房子和坟墓都背靠大山,唯独它面向大山背对来客。白色房子两米开外也有一座坟,那是房主的归宿。窗户玻璃内,一面颜色鲜艳的镜子里嵌着明星照,似乎也在张望这个世界。
51岁的张仕学和妻子默不作声,站在白房子前好奇地观望。张仕学有一只眼睛视力严重受损,所以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不过种地养牛是公认的一把好手。所以,他在山里养了三四头牛,还种点庄稼蔬菜。妻子被安排了一个公益性岗位——护林员,每月800元补贴,两个刚成年的儿子则在外面打工。
所有搬迁户的房子,都按照政策要求拆除了。而这座白色房子的主人未成为搬迁对象,所以,主人的儿子不同意拆除。张仕学夫妻俩劳作之余,会在这座房子里休息。
不过,他们并不在房子内做饭,说担心熏黑了别人的房子。只要天气允许,他们就露天做饭,锅碗瓢盆凌乱地放在地上,装着几双竹筷的橙色塑料盒子挂在铁架子上。
一只脏兮兮的流浪猫喵喵地小声叫着从锅碗瓢盆边溜走,它被主人遗弃了,或者说,它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做着主人。除了张仕学夫妻偶尔给它残羹冷炙,谁也不知道它是如何顽强地活下来的。
五保户,唯一的留守者

五保户张绍辉是唯一的留守者,他的房子非常简陋。他已初步答应搬到公路边居住。
在鱼跳村的最高处,有一座小小的房子,只有十平方米左右。在旁边两层楼那么高的巨石和门口高大的核桃树映衬下,它越发显得很小。
这座房子极其简陋,下半截是夯土墙。左侧是吃饭的地方,一张迷你的矮桌子上放着主人的食物,一大盆白米饭,颜色发黑的炒黄豆,还有一盆灰黑色看起来令人迷惑的汤菜。主人解释,那不是酸菜,是牛皮菜(学名莙荙菜)。右侧是一间空荡荡的小卧室,窗台上放着镜子、牙膏、杯子等生活用品,老式机械闹钟滴答滴答地响着。
房子上半截是木板搭的阁楼。通过梯子爬上阁楼,那里通向主人——71岁的五保户张绍辉的卧室。纵向分布的木板非常稀疏,外面蒙上一层透明的塑料布,这解决了采光问题。不过,风依然会从瓦顶和木板之间的横向缝隙灌进来。
阁楼的另一半堆着杂物,上面堆放着一篮子核桃,一大包宽面条就随意地放在布满灰尘的木板上。主人邀请我吃核桃,还打算为我煮面条,我以同伴还在公路边等待而委婉谢绝。
还有一只小小的腰鼓躺在阁楼上。年轻时会打鼓吗?张绍辉含含糊糊地回答着,而楼下张仕香和张仕学俩口子呢,不知道谁开玩笑说“叫花鼓”,然后哄堂大笑。
房旁的旧屋基上,小麦半青半黄,也许能收二三十斤麦子。菜地里,包菜长势惊人比脸盆还要大,莙荙菜已经抽苔开花了。看起来,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不过,房子周围布满了坟墓,难以想象在所有人撤离的夜晚如何安然入睡。
每个月生活支出大概三四百元。张绍辉说,每天要喝一斤酒,隔三差五去街上买点米面,二三十斤还是背得动。
张绍辉是一个性格开朗而幽默的人,问他一天吃两顿还是三顿?他慢悠悠地说,“吃三顿?怕吃四顿哦。”接着,又正儿八经地答道,“吃两顿。”
他并不介意谈单身话题,一边抽着旱烟吐着烟雾圈,一边继续慢条斯理地说,因为自己嫌弃别的女人。旁边的人又哄堂大笑起来。
不过,张绍辉并不是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村民透露,他谈过四个女人。这么偏僻而艰苦的地方,似乎娶媳妇不容易吧。可村民略带不屑地说,“还真的有点奇怪,我们这地方没有打光棍的。”
为什么不搬出去或者去养老院呢?他说,愿意搬出去,但是没名额;不过,不愿意去养老院。据了解,不是名额问题,而是没有针对一个人的搬迁政策,因为20平方米的户型也不好设计。
有人解释,张绍辉每月享受基本保障金875元,外加老年人补贴98元,加起来近千元。可是,如果去了养老院,每个月的补贴就要由养老院统筹使用,个人就没有支配权利了。
不过,张绍辉初步答应一个折中的搬迁办法,政府在公路边废弃的养鸡场收拾两间房给他住。这个最后的留守者也终将和滋养一生的鱼跳村道别。
安置点的新生活
55岁的张仕勇一家七口搬到了乡政府的安置点。以前,他和儿子讨论过房子的问题。如果在老家盖砖房,光是运费就不得了,材料费要翻一倍。商量的结果,还是要在外面买房。
幸福来得很突然。他们没想到,受惠于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分到同一单元两套门对门的小户型安置房。“最大最好的愿望,就是方便孙孙读书。还是非常感恩。”
广东籍的儿媳嫌太远太穷在搬家前夕离婚,儿子一人在外做理发师,每月收入4500元左右。全家有5口人被列为低保对象,每个月低保金总共800多元,全家老小一个月开支大概1600元。
他说,刚搬来时也不习惯,没工作,没土地。“走哪里都是为生活,土地让人安心。”主要靠打零工赚点收入,有零工做就勉强维持生活,没有零工的话就要吃老本。
鱼跳村民从不通路的山谷搬到山上的街市,从空间来说实现了鱼跃,从居住的质量来说也实现了鱼跃。田坎彝族乡的安置房非常扎眼,两排四层的步梯房,顺着坡道错落有致地分布着,风格统一,布局整齐,327个搬迁移民居住在这里。
安置房的一楼是商铺,每家都有平均十平方米左右的商铺。矛盾在于,这个乡人口太少,街道太小,市场空间非常有限,商铺什么时候能发挥商业作用还是未知数。
田坎全乡有2000多人搬迁到毕节市区,现有人口168101人。街道只有一条,沿着乡政府门口公路两侧大约分布着20多家商铺。
乡长赵耀解释,发展需要一个过程。2012年,田坎才开集市,过去要到临近的龙场营镇去赶集。鱼跳村适合种柑橘,因不通路,没人愿意去种。目前,政府正积极申报将鱼跳村纳入国家储备林,如成功,可以为村民增加一点补贴性收入。
除政府扶助之外,市场经济的曙光也在慢慢降临这个远离繁华的地方。去年7月,从江苏返乡的熊平在安置区开了一家做民族服装的扶贫车间,能提供十多个就业岗位。她并不担心订单,主要是出口,“内单不敢接,要得急。”今年,受疫情影响,工厂迟迟没有复工,接了一个做西装夹克的内单,转给了六盘水的一家扶贫车间。
为什么不敢接内单?熊平解释,田坎安置点的工人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手脚慢。但是,六盘水的合作伙伴同样是扶贫车间,却以年轻人居多。她现在最大的愿望,也是不确定的愿望,“看疫情过后,外单是不是会恢复。”
生活的疑虑,也埋在新移民内心深处。如果把鱼跳村的村民比喻成鱼,那么,新的生活究竟是顺流而下那样轻松还是逆流而上那样充满挑战?张仕勇迟疑地回答说,“还是往上跳。你跳,还要跳得好,不能乱跳。” 他也明白,“适应有一个过程,两年多了,基本稳定。”

鱼跳村整组易地搬迁,大多数人在田坎彝族乡安置点安居下来。
采访手记:帮助移民度过生活哺乳期
毫无疑问,鱼跳村易地搬迁后的移民生活,实现了一次堪比鲤鱼跳龙门的大跨越。对这一点,村民们也深怀感恩之心。
但是,适应新生活也非常不容易,村民体现出一种依依不舍的断乳心态。
移民内心深处还是缺乏安全感,他们总觉得周而复始的农耕生活是最可靠的。特别是今年疫情对外出务工带来的影响,令年纪大的老农民更加犹疑不定。基层干部要注意引导移民增强战胜疫情恢复发展的信心。
旧的房屋拆除后,生活方面“两头住”的现象得到遏制。但是,生产方面“两头跑”的现象还难以消除,估计短期内不会消失。基层要想办法创造就业,在移民从农村转向城镇的适应过程中还要适当哺乳。
搬出来容易,稳得住才是本事。只有解决了生产发展的信心问题,才能实现稳得住的短期目标,才能实现逐步致富的长期目标。
文图/视频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肖郎平 谢巍娥 周自立
责任编辑/胥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