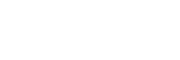何光渝:半个心想当“业余”记者 | 《贵州日报》创刊70年·我在文艺副刊的岁月
- 作者:舒畅 吴浩宇
- 编辑:胡岚
- 来源:当代先锋网
- 发布时间:2019-11-27 21:26:58
- 作者:舒畅 吴浩宇
- 编辑:胡岚
- 来源:当代先锋网
- 发布时间:2019-11-27 21:2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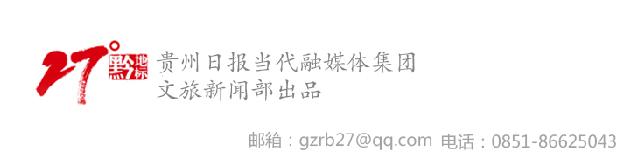

讲述人简介
何光渝,文化学者,贵州省省管专家、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先后出版《20世纪贵州小说史》《贵州:衣食住行的变迁》《原初智慧的年轮:西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与神话的文化阐释》《铁血破晓:辛亥革命在贵州》《贵州社会六百年》《中国抗日战争全景录·贵州卷》《如在天尽头》《山高人为峰》《天人合一 知行合一:贵州人文精神读本》《往事犹可追》等20余部著作。贵州文化是其大多数著作中的主题。

1980年初,我从《贵州日报》记者部调到了政文部文艺组。我的家从龙洞堡的红机厂“干打垒”宿舍,搬到了昌碧一亲戚家在东门螺丝山半山腰的临时拆迁过渡房。山脚是贵阳市文工团的驻地,隐隐约约可以听到那里传来的乐声和歌声。我在家的时候,白天总会抱着我不到两岁的宝贝,循着弯弯曲曲的路人踩出来的小路,一面走,一面在女儿的耳朵边喃喃地叨念:“上山山……下山山……上坡坡……下坡坡……”到了文工团的墙外边,再转转,一圈,又一圈……夜晚,宝贝哭闹时,我会抱着她,轻轻摇晃着,唔唔唔地哼着《摇篮曲》:“宝贝,你爸爸正在过着动荡的生活……”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那时,心中甜蜜又酸楚:我长年不在家时,那些日日夜夜,妻子、母亲和岳母不就是这样度过的吗?

在贵州日报社工作时与老作家蹇先艾在贵阳钢铁厂采访
大半年后,我家才又从那山上搬下山,搬到报社在延安西路打铜街口金沙街的老宿舍内。报社的老人称那里为“城隍庙”宿舍,一个住有十几户职工的小院落。

在《山花》编辑部。左起:何锐、叶辛、何士光、黄祖康、罗绍书
报社分给我的,就一间房,大约十二三个平方,一门一窗。不开门时,屋里要开电灯;开门时,则路人可以一览无遗。地面则是“原装”的泥土地,潮湿无比,同我以前住的“干打垒”一样,也要在地面撒生石灰以吸潮。现在有了小女儿,我就在赶场天到乡下,买了几十百把斤青冈炭,撒在地面和房间四角。墙是石灰土墙,凹凸不平,用手指一按一个坑,几乎要渗出水来。不到十步远处,就是小院的公共厕所,臭味终日飘过门前……我们一家三代四口人,就此蜗居,一张花布床单当做隔断,晚上睡觉时一分为二,白天开门时合二为一,却也其乐融融。早上,我会带着两岁的女儿,到街对面路口的一家路边汤圆摊去吃汤圆。那一阵,她就爱吃汤圆,或许是因为那首台湾小调流行的缘故,整天“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圆又圆……”晚饭后,妈妈带小女昕儿在邻居佘阿姨家门口看电视,昌碧在家里给小女做针线,我则趴在矮桌上写稿子……

与少数民族作家伍略、苏晓星、吴恩泽、艾克拜尔·米吉提、龙岳洲等在一起
不久,小院内有人搬走了,余下一间不到10平方的空房没人住。再不久,报社就把那房分给了我。从此,我家就有了两间小屋……后来听报社办公室一位负责人透露:我那间破房子还是陈老总拍了桌子才分给我的,旁人很少见他发那么大的脾气!你才来报社几天呀?他说的陈老总,就是报社的总编辑陈健吾。那时,文艺组隶属于政文部,我去时,有林钟美、张克、彭钟岷、罗马。他们都年长于我,是老师。后来,先后走了彭钟岷和张克,又来了刘仰向、徐菁。他俩及罗马都是1957年“反右”时的受害者,是“拨乱反正”后落实政策先后回到报社的。此间,先后来了又去的有黄维鸣、任远琴、田米亚。人员流动着,男男女女,各有个性:风风火火,温温吞吞,老成持重,年少气盛……却也一心办报,和睦相处。

与妻、女、孙
我坐在后排办公桌,杂务就理所当然地归我。编稿之余,我就在屋内看看书,较之当记者那两年,感觉轻松了许多,却又恍然若失,觉得自己没有了根,悬浮着,有点“失重”……于是,心里总生出一些想法、题目来,半个心想当个“业余”记者。
(摘自何光渝新著《大道长歌:我这四十年》)
附:老文艺部编辑记者眼中的何光渝
彭晓勇:我在文艺部时期,先后有十几位同事,记忆之中,何光渝老师的表率作用和对我们的帮助提携可谓润物无声。我们写的稿子,交给何老师,他基本不会大动,但会在标题或文内改那么几个字几句话,好多次,看了何老师改的稿子,只能由衷的赞叹改得真到位,他会把文气理顺,文意畅通,更加简洁,更为精当好读。何老师自己非常勤奋,我们在文艺部时,就不时看见他发表报告文学、评论、散文,等等,后来何老师离开报社到省文联工作,著述丰硕,这几年更是佳作迭出,而且涉及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等学科门类,他有意构建地方历史文化谱系,尝试着通过自己的学术努力,为贵州的文化历史梳理脉络张扬文脉,在文化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让我感动的是,我女儿出生时临近春节,我请假在家照顾孩子,报社那时年终福利往往会发一些食品,那年发了带鱼和一些别的东西。一个阴雨绵绵的中午,何老师带着他女儿何昕,把分给我的几斤带鱼和其他东西从贵阳送到花溪我的家中,那时从贵阳到花溪十分不便,公交车又挤又慢,顺当也要差不多一个小时才能到,何老师只说要过年了送来让你好准备年夜饭,工作上的事不要多想,好好照顾爱人和女儿。几句亲切的话语,几条带鱼,让我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温暖。
奚晓阳:何光渝主任给我的印象是谦和认真、满腹诗书、言简意赅。对年轻人的指导不是“诲人不倦”,而是恰到好处的点到为止,我们新创的《七色花》以及原有的《娄山关》因此常有出彩之处。明先贤吕新吾曾说人的资质有三等,一等是深沉厚重;二等是磊落豪雄;三等是聪明才辩。我认为此三等均融入何光渝的为人和学问中,尤以深沉厚重显示其自信从容,以及精神和文化上的坚守。
田米亚:文艺部给我改稿子最多的是何光渝老师。他内力深厚,武功高强。我一篇平平淡淡自我感觉都不咋地的文稿,一经他手,或调一下前后段落,或改几个字句,或换一下标题,则效果立显。这才是编辑的真功夫,够得学一辈子。可以说我在文艺部写稿水平不断进步得到提高,是何光渝老师一手教出来的。我后来岗位转变由采编到经营,虽从未脱离媒体,但逐渐远离了新闻采访第一线。从写新闻到写方案,对文字表达的要求不同,但当年打下的写作基础却使我至今受益匪浅。
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贵州解放70周年和《贵州日报》创刊70周年。正在进行中的“我和《贵州日报》”大型征文活动,收到了大量来自热心读者和作者的来稿。其中,“《贵州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是如潮的来稿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群体之一——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热爱读报和文学写作的投稿人来说,这个群体几乎是他们和报社之间最生动的联系,甚至还是他们走上文学之路的榜样和导师。
《贵州日报》文艺部,是今天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文旅新闻部的前身。当年才华横溢又人才辈出的“老文艺部人”,即使离开文艺部,离开了报社,也在省内外各个工作岗位上表现不俗。在《贵州日报》创刊的70年长河里,他们就是独特又耀眼的浪花朵朵。
特邀几位《贵州日报》文艺部“前辈”讲述在文艺副刊耕耘的往事,不止是怀旧,更是向《贵州日报》创刊以来的一代又一代媒体人,向《贵州日报》一路走来的光荣和梦想致敬。时代风云变幻,媒体盛衰更替,然而当媒体人曾经经历的真实在岁月的长河中被打捞上岸,仍然弥足珍贵,富有价值。(执笔:舒畅)
辑录/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舒畅
刊头制作/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吴浩宇
责任编辑 胡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