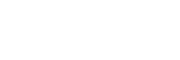梦中的淌淌河
- 作者:王仕学
- 编辑:周梓颜
- 来源:黔西南日报
- 发布时间:2019-12-13 20:26:23
- 作者:王仕学
- 编辑:周梓颜
- 来源:黔西南日报
- 发布时间:2019-12-13 20:26:23
淌淌河是鲁屯与洒雨曲的界河,也是一个寨名。更准确地说,那寨子叫下淌淌。是我童年神往的地方……
我6岁,快过年了,狗舅舅骑着那匹白马来,好威风!
“让小建和小英去我们那里玩几天,我们杀猪。”舅舅说完,我转眼望着母亲,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母亲沉思了一会儿,点头。我和妹妹兴奋,又害怕,毕竟是我们第一次出远门。
一匹马,骑3个人,舅舅居中,我和妹妹一前一后。过了鲁屯,那马在山路上坡下坎,我们心提到嗓子眼,妹妹抱紧舅的腰,我死死抓住鬃毛。平路的时候,舅舅从容地指点,说,哪是柘围,哪是黑石头,哪是三岔地,我们好奇盯着那些别样的风景。舅不过是比我大10岁的少年,属狗。
翻过一个三岔地山梁,一条大河蜿蜒流淌在山间,对岸的山腰,十多户人家,那就是下淌淌,狗舅的家。那白马缓缓下坡的时候,河对岸的幺公幺婆早就看见我们了。他们奔到河边,抱我们下马,幺儿幺儿地叫过不停,甚是欢喜。河上没有桥,只有平行的两根抠空的木头搭建的渡槽,一只脚一个槽,向前移动,槽下是翻滚的河水。不要看下面!幺公吩咐道。先将妹妹背过去,妹妹卷伏着,不敢睁眼睛。之后牵着我,中途我惊叫一声,摇晃了一下,幺公用大手将我扶正,像扶一株树苗。幺公年轻时是鲁屯一带出名的打油匠,臂力大得惊人。那白马从渡槽上通过,悠闲地甩着尾巴。
到了幺公家,肉、金黄的包谷饭,敞开肚皮吃,对于寒冬腊月塞满一半酸菜一半饭的我们,自是一番快活的滋养。寨里的人将河水用明渠引过来,选一个坡坎安上水碾,加工米、包谷、小麦等等,这里大石碾比起我们家一两人推的小石磨,自然更有气势。
我带你们去看坝基!第二天早上舅舅提议。爬上一座小山,那雄伟的建筑方方正正闪现在眼前,白花花水从那坝顶飞流而下,像一块巨大的白布,悬在两山之间,发出轰隆隆—轰隆隆的巨响,惊得我死死地闭着嘴。后来我才知道,这坝叫柘伦水库,当时我们只单叫坝基。
舅带我们参观大坝下的发电机房,从机房顺着梯子爬到坝顶,我们总是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看到碧绿的湖面,不时有鱼儿跃出。我们主要是害怕。
第三天到屋檐挖白山药。那山药盘在地里长,弄出来像一只只脚板,居然有一些长短粗细不一的脚趾头。舅指着藤子上汤圆似的苕宝说,你看,把它埋在地里,它在地下走三年,就长成脚板了。我要了几颗带回家,种在菜园里,那脚板苕倒是多次走进我梦里。
我们到河滩上放马,那里有茂盛的芦苇,捡鹅卵石,自在地听鸟叫。那些大大小小的水塘里,使劲跺脚,一边“嘘嘘”地发声,鱼群慌里慌张地东躲一下西躲一下,鱼们以为藏得天衣无缝,我们觉得好笑。虾是聋子,任你怎样跺脚发声,它们只顾挥舞着长长的须,慢腾腾地走动,要么静静地趴在那里。鱼虾看腻了,我们就在河滩的石缝里找青草,到麦地里找野生的马豌豆,喂马,马打着响鼻,友好地翻卷着舌头。当然还可以上岸扒在地里摘嫩豌豆嫩蚕豆嚼食,那鲜味很生猛。
读小学以后,我盼着放假,因为可以独自走30里路到淌淌河了。暑假水库要泄洪,水猛然从泄洪道冲出,许多鱼防不胜防,被冲昏,漂游到岸边,只管捡。幺公家有的是菜油,煎炒不用担心。我们也可以节约菜油,将鱼剖开,洗净,撒盐,用瓜叶包上烧,或者用竹签插上烤,都是美味。
蓝蓝的天,翻卷的白云,青青的芦苇,乱石嶙峋的河滩,远处是啃食青草的牛马。一群少年在这样的画面里野炊,或狂奔,多么诱人啊!
我协助幺公烤酒,十几岁了,可以做点事了。我帮着烧火,把上好的糯包谷清煮到开花,幺公拿簸箕凉开,直到冷透。将酒药撒下去,拌匀。之后装入坛子,封闭发酵三个月。一般是腊月,封好三个月左右,到了春天桃花开的时候,猛火蒸,酒便从竹筒里淌出来,叫桃花酒。幺公解释说,酒药少了,出的酒度数不高,时间长了会变酸。酒药多了,出的酒度数高,但味苦。拌好两三天就烤,出的酒爆味重。经过冬春三五个月的发酵,酒才清澈透亮,无爆味,不冲鼻,醇厚而回味绵长。幺公打一点刚出的酒,让我喝,热辣辣的,比起喝水,刺激,但也是一种挑战。挑战需要代价,因此买酒要钱。
小学毕业我到县城读书,暑假到淌淌河,幺公问,那学校多大?我说,千多人哩,下课大家都去撒尿,那茅厕里尿槽哗哗啦啦的,淌得挺欢。幺公听完,笑得胡子都抖起来。看着幺公的高兴劲儿,我抢抓显摆的机遇,摸出英语单词本清了清嗓子,咿哩哇啦读给幺公听。又摸出兴义一中的校徽和三好学生徽章给幺公看,还冒充解说员。幺公笑得胡子抖了好几次。
幺婆没有听清,逢人便夸,我家外孙读书厉害哩,小学毕业就到兴义读大学去了。
读初三那年,我陪老表去淌淌河拜年。到了那里,姑娘的爹正在挑粪,老表二话不说,赶紧去挑粪,他要争表现。我四处转悠,打算晚上才去幺公家。晚饭时候来了几个漂亮的姑娘,自称是表妹。仗着人多,嘻嘻哈哈的,故意你扑我一下,我扑你一下,大声说笑。最后拉扯着给我添饭,一个抢碗,一个按着我的手,一个舀饭,我左躲右闪,一副窘态,她们觉得这游戏好玩,笑得很狂放。主人家和老表只是附和着笑。幺公大概他听到我来的消息,披衣进来,看着那场景,就骂道,你们这些“风摆柳”“人来疯”,我外孙是读书人,是个金元宝,你们不要逗他乱了性情。
“哈哈!”“哈—哈……”她们笑得更狂放,加些野蛮风味。
“金元宝”“老爷爷家的金元宝……”大声念叨着,比划着金元宝的形状,跑了。“金元宝”呢,坐在那里,木头一般,呆呆的立着,有些怅然若失。
刹那间,屋里安静下来。门外晚风徐徐,月儿正明。淌淌河沐浴在朦胧的月色里,如烟如梦。
如今幺公幺婆的坟头芳草萋萋,我已年过半百,淌淌河在我的记忆里,依旧汹涌澎拜,波涛滚滚……